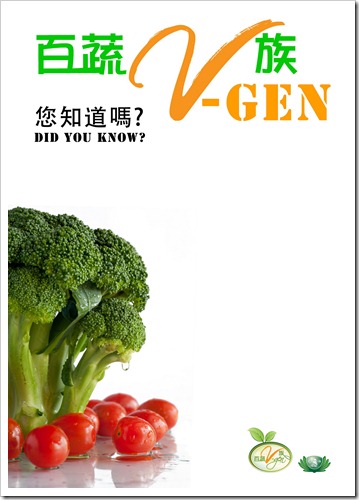一千多年來,漢傳佛教承襲印度佛教衍生出九個不同的宗派。直到台灣的「慈濟宗」成立為止,漢傳佛教逐漸從心性的昇華與追求,轉向以世俗社會的改造著手,達成自我生命與內在心靈永恆極致的成就與圓滿。
2006年12月,慈濟基金會創辦人證嚴上人,在花蓮靜思堂面對將近千位慈濟志業體的同仁及幹部,於精進二日共修活動結業典禮中,以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開示「慈濟宗門、靜思法脈」的意涵與其因緣。
「我們的宗旨就是走入人群,去知苦、惜福、造福,這就是靜思法脈,慈濟宗門…作為佛陀的弟子,要能體會佛陀在人間出生、在人間覺悟、傳法於人間,就是要開啟能夠在人間運用、度化世人的人間佛法。既知世間沒有『永住』的事物,也瞭解人生無常之理,知苦就要堪忍,修得忍而無忍的功夫,輕安灑脫,即能脫離『三苦』(註1.)。」(釋德凡,2006) 這一段開示在所有聽者心中彷彿是一道清澈明亮的聲響,這不是意味著佛教多了一個宗門,而是諭示著人類一股新的精神文明將逐漸在世界各地拓展開來。
這新文明為何?和漢傳佛教有何異同?對於當今紛擾之世界,「慈濟宗門、靜思法脈」,能提出何種思想、見解及行動,協助當今社會建構一個新思維和新人文?
從生死之迷惑契入長情大愛
1961年,是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十五年,在台中豐原的一位年輕女子,在父親過世之後驀然驚覺生命的無常,她開始更嚴肅地思索著生命的真實意義及最終的境地。那位年輕純真的女子就是今日慈濟基金會的創辦人—證嚴上人。那一年,她深切省思,為什麼人會往生?為什麼我們必須走這一遭?
記得當年禪宗五祖弘忍大師告訴弟子「世人生死事大」,要大家作一偈,以示是否開悟。結果出現一位才剛到禪院,每日劈柴淘米的弟子慧能,作出了「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偈語,令眾人大驚,弘忍大師只好故作無事狀,用鞋將廊壁上的偈子擦掉並說:「還是未見悟。」然後趁三更半夜將衣缽傳給已經頓悟的慧能大師(禪宗六祖),並要他連夜逃跑,因而開啟了中國禪宗的宗派,以及其後一千多年的興盛。(李中華,2006)
而,偉大的精神領導者,竟皆是從「生死」提問開始,總是不被周圍的人理解及接受,他們都經歷過孤寂的心靈歷程,而這歷程適足以培養其偉大的人格及超越時代的高遠思想。
慧能從「世人生死事大」之大哉問,提出「本來無一物」之覺醒,歷經逃亡的命運十多年,最後才在中國南方安頓下來,然後傳頌心法。觀照證嚴上人也一樣以生死之大事契入生命的無常,將不捨世間離苦的心轉為大愛之情。如他所說:「我也知道親情猶如一場舞臺劇,依業緣而聚。未來,我的人生要把愛放到哪裡?是要愛自己呢?還是愛我的家庭?或是愛我所偏愛的人?用心思考,這些都還不夠寬廣。同樣的一分愛,雖然當時環境不允許,但是我追求佛法的意志非常堅定。」(釋德凡,2000)
對世間無常、究竟空、畢竟空的情感及思惟,轉化為對眾生之長情大愛,堅定了證嚴上人對佛法的追尋。
思惟證嚴上人早年的際遇和對於生命本質的體會與慧能大師強調「本來無一物」之空性,證嚴上人從「無常契入空性」,從「空性契入妙有」,以《無量義經》的入世之法門,開闢慈濟宗門,確立靜思法脈,闡揚人間大愛,這與慧能大師對「本無一物」、「從無所本,立一切法」之空性闡揚互相觀照,又是不同時空各有其濟世度人之法。
真空亦是妙有,無常中正可以表現人性中無不歇止的覺有情。上人早年對生死之思索,成了他教導眾生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透過一切法門,讓眾生瞭解世間的一切,終究無從把握,終究過往煙雲,只有大愛和慧命長存不朽。慈濟四大志業:慈善、醫療、教育及人文,都是為了認識一個永恆的生命之存在;體悟諸法究竟空、畢竟空,但又妙有真實之境界。
這種體悟並不是教導弟子去漠視人間、冷淡對待人生的苦。上人積極地要慈濟人搶救生命,不論是地震、風災、水災或戰禍,慈濟人以無畏施的心情,在搶救生命中,看見生命的無常,終至體會「萬般帶不去,只有業隨身」的道理;並發願追求一個更為根本和清淨的心靈歸宿。不捨眾生,在搶救眾生之際,能復為說法,使人人最終都成為能樂於幫助人的菩薩。
戰火下醞釀之思惟
證嚴上人生長在一個戰亂的後期,他年輕的時候一樣躲過空襲,他看到有一個人為了躲炮彈,跑進防空洞裏,手裏還拿著一把菜刀,應該是煮飯來不及放下菜刀就跑出來,而且另一隻手臂鮮血直流,原來他只顧著躲炮彈,竟不自覺地讓菜刀把自己手臂砍傷。證嚴上人幼年時小小的心靈看到生命的脆弱及人性互相殘殺的傷痕,不禁自問:為何生命必須殺害生命?為何人與人必須互相壓迫對抗?沒有人可以正確估計這一段臺灣戰亂的歷史對於證嚴上人的意義有多深刻?但是一個和平互愛的社會,應該是他早年的歲月中就已經深切渴望的。我們必須感恩那一段戰爭歲月並不算長,證嚴上人也不須一直躲戰火,這使他的生命能在一個更穩定的環境中,自由開闊地發展其人格及思想。
1960年代的臺灣經濟開始逐漸富裕,證嚴上人的俗家父親生意做得不能不說是很好。將近十家戲院同時經營,證嚴上人小小年紀已經學會事業管理及待人之道。他對俗世的瞭解是在那時候奠定的;對於俗事世界充分瞭解,使他能夠在入世志業中不致過度理想化。而上人離開家庭證應了他對俗世的超越,一如佛陀生長在皇宮,使他歷經人間繁華,但這一切都在更遠大的真理追求中顯得微不足道。
老子曾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2004)這話的正確意義應是說有了功不居功,生成又能不佔有,有了作為才說不憑恃,若無功的人說他不居功,這是不切實際的。能從有而入無,才是真正覺悟的無。
證嚴上人的成長背景與佛陀的人生際遇是有相類似的。我們並不是說一切孕育偉大的土壤都似乎早已預備,但是偉大之所以成其偉大,除了天生內在之力,也自有其造就它、成就它的特殊際遇。
佛陀來人間是一大事因緣—開示眾生悟入佛之知見。為何是一大事因緣?因為這因緣必須匯聚各種條件,這些條件是那麼的不可思議,那麼恰如其分地組合在一起,才造就佛陀來一趟人間。對於一個身為證嚴上人的弟子來說,要分析追溯上人到人間的因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分析是何種人間引導一位偉人開創出人世間的新文明,卻是我們必須思惟的事。
慈濟發軔於臺灣的歷史因緣
證嚴上人出生在東方世界的一隅—臺灣,這個小島,歷經西方殖民統治將近四百年之後,對於西方的資本主義及科學主義有相當程度的熟悉和不排拒。而中國之儒家思惟在海洋及政治雙重隔絕的歷史因素下,使得臺灣有儒家之傳統,但一直未讓儒家處於文化的支配性地位。漢傳佛教在中國這一片古老大地經過將近一千七百年的發展,也對臺灣文化及人民之生命觀有相當深遠之影響。
這三股文明匯流在中國邊陲的臺灣,在世世代代的子民為生存奮鬥的過程中逐漸融合演進著;這些文明的土壤正是孕育慈濟在臺灣生長茁壯的結構性力量。而證嚴上人以幾乎是天生具有的大智慧及無比的人格特質,不自覺地、創造性地,將這股薈萃的人文運用融合,並且發揚光大。
正如文藝復興發軔在義大利的小城邦佛羅倫斯,臺灣作為中國古老帝國的延伸,有它自己獨特的歷史命運;這命運使它更早經歷資本主義及科學主義的洗禮。它沒有中國大陸抗拒西方的激烈過程,也沒有發生五四運動中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全盤西化之間的掙扎矛盾,及其所引起的中國社會巨大撕裂及戰爭。
臺灣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但是不同於儒家在中國大陸是基於支配性的思想地位,臺灣比較沒有儒家在封建社會中,那種以「家天下」的深沉文化結構,因為它多半時間是被西方列國統治。它也沒有直接擁抱西方之社會文明,而是以日本作為橋樑,接受歷經「明治維新」修正的西方社會體制。佛教信仰在這裏逐漸被民間信仰及道教所融合,逐漸失去其獨特性及深厚的思想基礎。
佛教在臺灣有被消融、式微之慮。然而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卻為一個全然的文明思惟之生長,提供豐富且相對自由寬廣的空間。慈濟在臺灣的誕生、發展,無疑是歷史的偶然,也是歷史的必然。
慈濟與儒家之淵源
1966年證嚴上人創立慈濟功德會,以「利他、度己」的理念,強調世人應「無所求的付出」。這和資本主義「先利己、再利他」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無所求的付出活化了佛教三輪體空的意義,讓佛教走進現代化,並賦予深刻被理解性及實踐力。
證嚴上人帶領會眾走入人群,這和傳統的佛教強調往生西方世界,強調內證自明之直觀宗教有明顯的不同。證嚴上人認為淨土在人間,淨土在當下之一念心。他不只要慈濟人走入人群,更要志工把家庭顧好才能做慈濟,有別於傳統佛教最高修行境界強調之「捨親割愛」。家,是證嚴上人強調之社會重要的核心價值,這是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所致。上人早年勤讀《法華經》及《無量義經》之同時,也熟讀《四書》,這對他的思想有深遠之作用。
慈濟世界雖重視家庭,證嚴上人總是要志工們先把家照顧好才能做慈濟;而不同於中國封建社會「家天下」常隨著裙帶關係的觀念,只要有人得升進士,就能庇蔭家族,因此中國傳統儒者政治有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之譏。然而,一人體悟得道,庇蔭社會得大愛,則是證嚴上人所強調。
上人教導弟子以愛家人之心愛天下人,「拉長情、擴大愛」,這將儒家在歷史上被扭曲的負面發展提供了修正,也將中國傳統社會之裙帶主義做了智慧的提升。在慈濟世界裏,我們都是一家人,但這個家,不是營一己之私的家,而是擴大愛心,去愛更多人、一起去無私奉獻的「大家庭」。
儒家的另一個思惟,是要知識分子或士大夫在一生中達成「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然而,儒家又是不強調輪回及來生的觀念,孔子總說:「未知生,焉知死。」似乎對於儒者而言,人就只有這一輩子;這一輩子總是要做到「三不朽」的任何一項,人生才沒有空過,生命才算有交代。對於現世的關懷及投入,成了儒者最重要的精神依歸。但是如果一個知識分子在僅有的一生最終未能立功、立德或立言,那他的良心及價值體系勢必產生巨大的傷痛。
在古代王朝中,士大夫之抱負、見解及貢獻的欲求,經常轉化為黨爭、政爭,此等因積極入世的趨力所產生人與人激烈爭執的人性劇碼,在歷代王朝中層出不窮。然而這樣的心理壓力,讓儒者充滿了胸懷治國平天下的道德勇氣,一方面也給予自己巨大的成就動機之壓力,以致知識分子擠在朝廷裏,一生為君王、為國家奔忙,或挫折、或哀傷、或失勢、或憂鬱,沉沉浮浮的宦海生涯,折磨著每一個士大夫,這多半和淑世的強烈企圖心有關。
慈濟對傳統儒家之省思
與儒家「三不朽」之嚴肅使命相比,佛教有一個觀點說「菩薩遊戲人間」,藉種種身形教化有情眾生,其實,人一生所經歷的一切功名成就,都是假象,都是短暫的,一切只為歷練一個更永恆的生命智慧。一個人不可以不擇手段地立功、立德或立言,因為今生造業,來生還要再報。佛教思想給予個人更高遠、更嚴謹的思惟,也是更為徹底的道德境界。
善與惡,作為與不作為,都會在宇宙因果定律中兌現,都會在心念意識中永駐常存。不管世俗世界對你的作為知不知曉或如何評價,惡業或善業一切都有其因緣果報。我們的心念,生生世世回繞在永恆的意識及慧命中不斷鍛鍊。
體悟這一點,一個人自然能夠以更超越、更自在,或者更悠久的方式為生命努力。並非求功名、求文采、求美名才是不朽;不朽來自內在自性的清淨無染,永恆的追尋和奮鬥,是不離內在自性。不管身處貧窮或富貴,仕途得志或不得志,都只是為歷練心無所執的過程。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自性原本就圓滿自足,何須外求。這種思惟及境界,讓人們從世俗世界的捆綁中釋放開來,不致被世俗環境無止盡的牽扯,載沉或載浮。這種思惟,為人們指出一條更加寬廣,更加超越的自省之法和究竟覺悟之道。原始佛教大乘之法,並沒有要我們脫離世俗世界,而是證嚴上人所說:「用出世的態度,做入世的事情。」這是不執有、不執空,既淑世又超凡的生命境界。
從出世到入世
佛陀在《無量義經》所言:「甚深無上大乘微妙之義,當知汝能多所利益眾生,安樂人天,拔苦眾生。真大慈悲信實不虛,以是因緣,必能疾成無上菩提。」(證嚴法師,2001)無上菩提智慧之道是以利益眾生為要。
證嚴上人早年身處的世界,佛教逐漸被道教及民間信仰混淆,甚至淪為往生者的一套空虛的超度儀式。人往生了就找法師來念個經,一般人竟以為佛教是死後的超生儀式,而非生命的依歸。文人於仕途也深信,進於儒,退於道,止於佛,佛教是一切繁華落盡之後最後的慰藉,是一切生命的熱情消融殆盡之後,僅存的餘溫…
證嚴上人從自行剃度以來,從不趕經懺,他不願意佛教經典淪為腳尾經(人往生了,法師在腳邊誦經之意)。佛教必須更積極入世利益眾生,成了上人重要之生命目標及理念。佛教徒的一生追尋,也不是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上人說極樂世界在當下,涅槃寂靜不一定在死後,當下一念不生、一念不起,就是涅槃寂靜。
上人將佛教帶回原始精神之入世情懷。只有透過利益眾生,才能證得無上菩提。從另一個方向思考,慈濟人文是復古佛在世時的教義與精神,四大志業更是以創立適應現代社會生活背景的方式來教化大眾。
漢傳佛教正經歷文藝復興
正如西方文藝復興的西塞羅所言:「感謝蘇格拉底把哲學從天上帶到人間。」文藝復興之前的基督教修道士潛心於修道院中,自修禱告,追尋他們和上帝的合一,對於人間苦難並不特別關注。一直到文藝復興之後,才把宗教之實踐從追尋人與上帝之合一,轉向到對社會疾苦及人群福祉之關懷。
這一點和慈濟之於佛教發展有相同之脈絡。慈濟或許正是漢傳佛教的復興,然而不同於傳統漢傳佛教思想以建廟誦經拜佛為主,證嚴上人著眼於對現實世界苦難之救贖及改革。對慈濟來說,道場不必然存在於廟宇之間,而是深植在人心之中。災難現場是道場,只要勇猛無畏地展現慈悲,當下之心即佛心;煉獄即莊嚴佛國。一如醫院是苦的總匯集,但慈濟人要將醫院轉為天堂,這正是地藏王菩薩所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真實寫照。
慈濟將佛教精神轉化及昇華,賦予現代化的實踐方式及價值。慈濟的環保回收及大體捐贈,把無用之物轉為大用,從這類活動之間,體會生死究竟有何差異?這相印佛教思惟裏所謂「生又何嘗生,死又何曾死」,生死來去之間,只是印證生命之永恆價值在於個人對於慧命之體悟及把握。
從迷信到信仰
證嚴上人一方面努力去除佛弟子在形上思維落入斷滅空的陷阱,將一生的努力沉吟在直觀內證自明的神秘開悟經驗之中;一方面也避免把佛陀當作造物主或主宰神一樣地膜拜。
臺灣佛教徒或許多民間信仰者常常燒香拜佛,以求得平安發財。這種做法是把佛陀當作一位神祇,而不是一位生命的大覺悟者。其實禮敬諸佛是為了清淨自心,將佛陀當作一生修行的典範,所以證嚴上人更希望大家「不要求佛,而是要做一個能幫助別人的人。」
這不僅體現利益眾生的教義,也肯定了眾生皆有佛性、人人都有本自具足的自性力。上人期許慈濟人實踐付出利他之心,不要依賴神明神力,不要貪濁欲求,終不得解脫;他鼓勵慈濟人從利他入門,並且從利他中淨化自心。
早期許多喜歡算命的弟子,後來皈依上人,從此不再算命、問命運。上人告誡弟子,人要「運」命,不要被「命運」支配。他說命運是有的,人的一生的確有劇本,但是憑著願力我們可以改變它。這思惟既不是命定論,也不否認命定之存在。「萬般帶不去,只有業隨身」,是上人常常強調的。
一個人學佛之後,並不是從此平安快樂,不會再有無常、不會再有逆境。學佛是要學會用正確的態度,面對生命無常的到來,然後更要融入共善匯聚的眾多因緣中,超越命定之業力,多多造福,積累福德,如此即使有重業也才可能輕受。做慈濟、行善並不是買保險,從此事事順遂,而是要能深刻體會「利他」是證悟菩提必經之道。
許多佛教國度裏充滿了貧窮及不平等。信佛難道不能改變人的處境嗎?證嚴上人不只要弟子行善積德,他更要大家以團體之力行善,創造共善之環境去改變貧窮及不幸。
慈濟人曾經到中國大陸貴州賑災,志工回來告訴上人,貴州太窮了,土地貧瘠、多山多石頭,無法耕作。他們說貴州只能用三句話來形容,「開門見山,出門爬山,吃飯靠山」。貴州的窮是歷史性的,難以改變。但是上人卻說,歷史也是人造的,只要發願,有願就有力,就能改變歷史。慈濟於是在貴州進行遷村,將住在貧瘠山區的農民搬遷,找優質土地,蓋新房,重建他們的生活,改變他們的命運。這是「運」(轉)命,而非「命運」(被命所運轉)又一次真實的實踐和寫照。
上人認為覺悟在當下、行善在當下、淨土在當下,以務實之心,經由實踐改變人為造作所產生之不幸、貧窮或業力,因為一切都是人心之造作。上人不崇尚神通,一切以科學事實做基礎,不管是治病,或人生的規劃、逆境之超越,都是以正向務實之思惟為念,取代中國社會求神問卜,企望出家人展現神通廣大之神秘力量為眾生脫困離苦的想法。
上人啟發弟子「福人居福地,非福地福人居。」這種正向、自信的思惟,鼓勵許多志工放棄迷信風水的習俗;而「逆境增上緣…不求事事順利,只求毅力勇氣、智慧敏睿……精進不懈。」這些都給予那些面臨逆境的人,不經由求神問卜,而是憑著一己之信心及智慧化解橫逆,展現自信豐沛之人生。
慈濟世界的科學精神
務實解決自己及社會的命運,是證嚴上人非常重要的理念。也因為如此,上人對於科學的努力及投入不遺餘力。經由科學的方法改善人的生理及環境之災害,上人創設慈濟醫院及許多分院、成立骨髓幹細胞研究中心、創辦理性研究方法的大學、建立高科技的大愛電視臺。
而在慈善方面,國際賑災的工程研發持續在慈濟世界裏發展。例如支持賑災的臨時帳篷,若遇到炎熱天氣,篷內溫度可能高於篷外十五到二十度左右。當時慈濟在伊朗賑災,就發現帳篷外是三十幾度,但是帳篷內已經五十多度了。因此日後上人特別請志工設計能通風、有雨水回收設備,又能以太陽能發電的簡易屋,並且利用回收紙製作,所以很環保,屋裏和屋外溫差在五度上下,屋底也墊高以解決帳篷容易進水的問題。
在環保方面,慈濟志工在上人啟發下,將每年回收的數億個寶特瓶回收處理,抽成細絲狀,然後製成衣服、毛毯以進行賑災。這些都是證嚴上人對於科技運用及獨特之創發。
科學主義表現在慈濟世界的另一面是不尚神通。佛教過去被詬病是因為強調許多神通,神通並非不存在,但是太強調就會執迷。其實若能以智慧瞭解各種邏輯觀念,並且依正道而行,自然能處處通達。
《探索頻道》(Discovery Channel)採訪慈濟過程中,得知證嚴上人每天上網看資料,用PDA(掌上型電腦)記事,以網路視訊和海外志工開會,經常收看由衛星聯繫的各地大型活動現場實況,上人對於科學是力行實踐及大量運用,令他們印象深刻。1998年上人創辦大愛電視臺,進一步以現代傳播科技傳達人性之真美善,這也是佛教運用科學利益眾生的一大突破。
科學主義在上人身上的另一個體現和思惟,就是不尚神通。證嚴上人不言神通,即使在他早年於花蓮新城鄉康樂村山下小木屋修行的過程,曾經有小木屋數日放光的奇特事件發生,但上人絕少言及。他曾回答來訪的《亞洲週刊》記者說:「那不是修行的目的。」
上人不尚神通,但並不是說慈濟世界裡否認神通的存在,只不過是不追求神通之境界。
佛教論述裏曾將人類視覺生理分為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這是什麼意思呢?肉眼人人有之,但肉眼所能見之事物有限,所以肉眼不及天眼。天眼能預見肉眼未能見或常人未覺之事物,天眼能預知某些事物,但不見得透澈宇宙萬物的運行規律,所以天眼不如法眼。法眼是指能洞察一切因緣果報之宇宙萬物內在運行之軌跡,但能夠洞見因果軌跡,卻未必有智慧能去避免或化解無常,因此法眼不如慧眼。慧眼不只洞悉因果規律,還能有智慧知道如何避免問題或化解災厄。(聖嚴法師,1999)但是慧眼仍不如佛眼,為什麼?因為佛眼就是愛,愛才能真正引領眾生解脫知見解脫。
證嚴上人直接教導弟子佛陀愛的智慧,跳過容易使人沉迷的超經驗境界,直接指出究竟終極的覺悟之道,就是佛陀無私的平等大愛。
慈濟思想與西方的自由主義
慈濟以團隊行善,強調團體合心協力之重要性,其本質是植基於東方精神。這給予信奉西方自由主義及個人主義之人們,在面臨價值虛無及空洞之際,產生很大的啟示。慈濟人認為個人其實是在群體中才能得到自由,一如上人所言,「一滴水能夠不乾涸,是因為投入廣大的江河大海。」(證嚴上人,1995)
慈濟人見證群體無私付出之能量,在世界六十五個國家發展慈善及醫療等四大志業,證實群體協力之成果。在群體中,個人之能量,反而因為無私、因為大家的相互成就,而且能力及性格都得到更大之成長及發揮。在慈濟制服背後所彰顯的是一個平等的心,而制服外觀所凸顯的是愛心的符碼,是人性利他的最高榮譽和象徵。
但是文明的許多發展卻把我們推出那個巨大的集體能量。現代文明教導我們—「人」的根本是自己、是自我;但自我竟是孤寂的起點。 《聖經》所言,當亞當夏娃吃了禁果,開始認識自己之後,他們開始分別了你、我,分別自己、他人和自然萬物是不相同的;這種認識竟是自我孤寂的開始,也是原罪的肇因。(Eric Formm,2006)
在歷史的進程中,我們不斷地背道而馳,將自己與一切整體之能量分離。當人類發明文字,就與萬物的實體分離;當我們發展了科學,就脫離了使人們渾然一體的宗教;當我們發展工業,就脫離了家庭;當我們發明了電視,就脫離了學校;當我們擺脫了貧窮,我們也脫離了一切權威所加諸的束縛。
聽過金錢使人自由嗎?金錢畢竟沒有使多少人的內心真正獲得自由。終於,聰明的人類逐漸找到一個屬於個人的獨立的價值觀,獨特的專長和特立的人格。但就在個人化逐漸成形之際,人們卻發現最後他必須孑然一身,面對一個充滿孤獨、茫然又危險不安的世界。
不止於此,在強調個人主義的當代,人們用盡各種方式逃離自我;渴望在無止盡的情欲追逐中,透過彼此身心的水乳交融放棄自我,極欲在酒的迷醉中拋掉自我,沉湎在吸毒的狂亂顛倒中脫離自我,甚或埋首在工作的匆忙中忘記自我。
即使中規中矩的你會說:我沒有藉由這些放縱物來逃避自我。但是當我們翻開報紙,打開電視,就開始和群體社會相連結;當我們拿起信用卡,因著電視廣告所推介的商品而進行消費時,我們就不再是一個特立的自我及個體。一切都在群體約制中形塑著「我」。沒有人能以一個孤獨的個體存在這個世界。
而弔詭的是,在自由主義的旗幟下,個人一方面以自我之實現及自由作為最終的價值。極力宣稱擁有自我及獨立個體。但是一方面,人們又用盡各種方式在逃避自我和孤離的窘境。而在追逐自我個體發展失敗之後,當代人們嘗試著用一種散亂的、無秩序的、瑣碎的集體氛圍,取代過去秩序井然、價值縝密、群我和諧的團體模式。
在工業革命及理性主義發展之前,人類還是屬於群體社會的,在西方中世紀人士是屬於教會及家庭的。在十八世紀以前的中國,個人很難想像離開宗族的自己到底是誰?即使是李白這種浪蕩不羈的才子也要說「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酒不是一個人獨飲的,是和朋友、詩及大自然相通連的。所以李白最後才會說,「與爾同消萬古愁」,這麼愁,還是和朋友一起消愁,李白再愁也要和朋友一起消愁。因為那時候的人不被視為是「個體」;個體和群體是不可切割的。
舊約聖經》說,「父親吃了酸葡萄,連兒子的牙齒也酸壞了。」父親的行為會連帶影響孩子,換句話說,個體不存在,個人屬於家庭。而在中世紀的西方人很難想像,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以及一個沒有教會的社會將是什麼模樣?且聽猶太教的牧師(Rabbi)是怎麼說:「把鄰居當作自己來愛他們,因為所有的靈魂都是一體的。每一個人都是原初靈魂的一個火花,而且所有的靈魂天生就具足這個靈魂。」
在東方,兩千四百年前印度太子悉達多在菩提樹下修行,有一天他夜睹明星而開悟在繁星點綴的星空中,他澈悟了宇宙的究竟之法。佛陀覺悟到,萬物原本都是一體的,一切都在不可思議的因緣中分離著,同時又契合著。
東西方的古老智慧不斷告訴我們,個體和群體之不可分割及相互依存之道。西方心理學家容格(Carl Gustav Jung)說,每一個人如果要獲得生命的完整,或要取得更巨大的能量,就得讓心識通向集體潛意識。
當一個慈濟的醫師在臺上和志工、護理同仁,甚或病患一起比手語,和著美麗的樂章表演出生命的感動,我們知道他是重回到群體懷裏,那是個體融合進大我之美。
當一群慈濟人在災區或環保場一起虔誠祈禱,我們說他是沉浸在大我的愉悅及虔敬中。
當慈濟人穿著整齊的制服出國賑災、親手膚慰感恩戶,同體對方的悲,理解對方的苦,我們說這是回歸到一個大愛的能量磁場裏,而那個大愛原本就在他的心裏;那是一種無私的給予,一種空,正如每一個珠子裏的那個空,能讓線穿過,能將大家都串在一起,編織成一個「大愛」廣闊的網,環繞宇宙一切有情眾生。
這是上人所創造及允諾的大我群體之美,也是個人通向自由及覺悟自在解脫之道。
西方的自由是來自社會及政治制度之保障,他的自由是外在的。但是佛教的自由卻是「定」,定亦即不被欲望捆綁的自由。佛教之所以強調「定」,而很少用「自由」這個字義,是因為真正的自由是來自內心。只有內心不再被欲望、執著、恐懼及妄想所佔據,人才真正自由,以佛教的言語來說,即是解脫。但是這項自由以慈濟意義來說,是在群體的愛中求得的。愛,是個人自由的核心。無論就環境或個人內心都是如此。
上人強調內心的自在,亦即自由,是因為愛。環境中有愛,個人便會處得很自在;個人心中有愛,他的生命就很自由喜悅。當代佛教思想泰斗印順導師,生命最後的歲月是在慈濟度過。他生病期間住在慈濟醫院,老人家醒來就是微笑,一方面是他的修行功夫到家,內心禪寂;但是另一方面,上人也強調,醫院裏的醫師、護士,其所有慈濟人營造一種愛的環境,讓導師住得很安心。可見上人認為個人獲致自由是環境的營造;內心能夠靜定,環境是一個因素,而且環境中「愛」的塑造,也是不可或缺。
因此,上人並不完全從內心修定作為人唯一達到內心禪寂、常在三昧的唯一途徑,環境的改造及作用仍是必要關鍵。這就是為什麼上人希望弟子能入世利他、無所求地去愛人;不只讓自我心中得到自在,也讓他人得到自在的原因。其「苦既拔已,復為說法」。(證嚴法師,2001)環境與身體的苦先拔除,再給予法髓,使他獲致最終內在本性的定靜及智慧,即是通向內在自由光明的究竟之道。
慈濟理念對資本主義的反思
西方哲人培根(Francis Bacon)從十六世紀當科學主義尚未到來之際,就預言科學世界的無遠弗屆將會根本改變人類。而十七世紀牛頓發現萬有引力至今,三百年來,世界的人口從1680年的四億人,至今到達六十多億。一個多世紀地球人口成長十六倍(Fernand Brandel,1979/施康強譯,1999)。人類在科學昌明之後,所耗費的資源比起之前的人類總消費要多上數億萬倍以上。
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鼓勵消費,人們非常辛苦勤奮功用,從薪資、股票權、金融投資市場努力賺取大筆金錢,然後一轉頭就拚命消費。發展,成為資本社會唯一的價值及信念,但是其最終結局是讓人落入工作消費無止盡迴圈中不得出離。一方面地球能源無止盡地耗損,大自然無止盡地遭破壞,已然成為當今人類繼續生存最大的危機。資本主義以利潤及消費作為基本生命之模式,已面臨嚴峻之挑戰。
2006年12月,世界環境組織在巴黎召開會議,針對全球氣候暖化做出結論,一百多位科學家們一致認為,地球熱壞是人為因素所導致。人類過度的消費,無止盡地擴大生存面積,所造成對自然之破壞及所製造之大氣層二氧化碳含量,已經使人類之生存面臨重大的危機。格陵蘭北極冰層之快速消失,意味著地球許多的低地將迅速被海水淹沒;美國紐奧良的洪水悲劇只是《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電影中預警的前奏曲。
其實證嚴上人早年在講述《法華經》時就說,天災始於人禍。而當今世界環境保護組織的結論中,證嚴上人的憂心及洞見似乎得到科學的見證及批註。
天災從何而來?從人心之貪、瞋、癡等念頭而來!人心各種毒念自古有之,為何於今尤烈?無疑地,科學的技術提升使人們的欲念更能得到擴大及滿足。藉著科技的進步,人們得以集體屠殺牛隻;許多豬隻終其一生都被關在一個僅能容身的鐵籠裏,甚至一生都沒有機會站起來過;商人用抗生素刺激雞快速生長,以便早日成為炸雞店裏的美食佳餚…
人類的生存竟是用數以億萬的生命作為代價!但其結果隨著森林消失,各種新興病毒如伊波拉、愛滋病毒等快速進入人群。隨著牛隻數億的成長,使得助長溫室效應的甲烷不斷增加;溫室效應的擴大,也使得氣候逐漸起了激烈的變化,並快速威脅著人類整體的生存。
社會的結構使人心的貪念更加擴大。現代社會的兩大結構「科學主義及資本主義」加速人心的貪念得以滋長蔓生,並且最終威脅到自己的生存。
催生資本主義的大師—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裏面最早提到追逐自我利益與公共利益的關係。亞當史密斯認為追求公益其實必須來自私利的極大化,他以一位善於做弓箭之獵人為例,初期這位巧手之獵人做弓箭是為了興趣,他因為善於這項工藝,逐漸被獵人族群欣賞肯定,雖然偶爾他也會做一些弓箭送獵人朋友,獵人朋友為答謝他也會回贈一些肉品。漸漸地,這一位善於工匠的獵人,發覺他製作弓箭所得到的肉品比自己打獵要來得多且容易。於是他就專心地變成弓箭製造的工匠,亞當史密斯說,社會的分工就從此開始。(Smith A.,1789/謝宗林、李華夏譯,2000))
亞當史密斯作為資本主義的理論先驅,他的理論諭示著資本主義的「分工」,意味著每一個人各盡所能,終究會得到自己及社會整體最大的利益;追求自己利益之完成,同時也會利益人群。這是影響資本主義結構極深的《國富論》一書中最基本的看法,亦即公眾利益是來自私利的極大化;私利的明智運用不但造福自己,也同時利益眾人。其實資本主義的環境底下,私利極大化的發展並不必然造成公共利益的產生。
兩百年來,資本主義標榜的私利極大化所造成的結果,不只是公共利益未如亞當史密斯所預言的出現,反而造成世界貧富極度懸殊,生態環境前所未有之破壞。根據聯合國統計,全球有二十億人口活在貧窮邊緣,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資產掌握在百分之二的人手中(Jeffery D. Sachs,2005)。每四秒鐘就有一位孩童因為飢餓而死亡。我們身處之世界比起亞當史密斯的十八世紀之社會更不公平,財富也更不平均。
資本主義社會受到達爾文主義之影響,物競天擇、鼓勵競爭。認為競爭是創造好產品及最有利於消費者的制度,在資本主義橫掃千軍之際,我們一方面要拚命工作,一方面拚命消費。如此迴圈周折、耗盡心力。我們信奉的科學,引導人們放棄宗教之禁錮,相信自己、信仰崇拜自己。實現自我,成了當今人們唯一的信條。
一如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為自我追尋提出最有利的論證,他認為人必須先追尋生理安全感、心理需求、愛的需求、自我實現,最後才能完成社會實現。實現利他之行動,永遠擺在自利之後。自我像是今天的廣告明星看板,被高高巨大地舉起,其影響力高過上帝,高過其他任何形式的宗教信條及信仰。(Maslow A.,1943)
在這樣的情況下,各種光怪陸離之追尋及欲求滿足不斷衍生,人們將辛苦賺來的錢,在資本商業市場廣告的牽引下,盡情消費,滿足自我,不但造成社會貧富巨大差距及大自然萬劫不復的耗損,也造成自我在物化之後極度的空虛。憂鬱、自殺、集體墮落,在資本主義專業人士身上不斷擴大習染著。那是一場無聲無息的毀滅和疾病,它以自我滿足為目標,實則扼殺自我的真實需求和本來清淨之面貌。
在後資本主義時代及科學主義過度發展之後,人們開始反思這兩大現代人的神祉之荒謬及錯誤。許多人提出見解,但是未必能對於資本主義之持續擴張及科學主義之無窮魅力,有任何之修正或找出可能的出路。
有別於資本主義強調自我欲求之擴張及滿足,也不同於自由主義強調個人之權利意識,必須得到最大的保障及伸張,慈濟的思惟強調自我真正的目標是內心的清淨,而這清淨是源於愛及戒律。欲望的擴張讓人永遠被欲求及貪念捆綁,不得出離。
真正的佛陀精神其實是要先淨化個人的內心,佛陀教導每個人真正不被情境所轉、不被欲求所困,這種絕對的心定,來自「戒」。所以「定」比自由更寬廣,也更根本。這個理念在慈濟世界是從無所求的付出鍛鍊起,進一步在群體中磨練自己的缺點,正因群體個人都參差不齊,所以可以將一個頑石磨成鑽石。而在愛之中,個人才得到解脫及自在。
沒有愛的社會或組織,對於個人就是捆綁,儘管現代自由主義精神宣導政治自由,經由法律途徑保障個人權利,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組織中,在職場裏,我們無可迴避地全部捲入了「人我衝突及組織利益至上」的框架之中不得出離。在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誰真正自由?誰真正尋得自我的終極價值?誰不被競爭壓得喘不過氣來,最後以物質消費作為補償的代價,其結果很像是追逐著自己尾巴的老鼠,永世脫離不了苦欲輪回的命運。
自我,不是來自個人對於社會約制的擺脫,而是個人掌握自己心志的能力;價值,不是來自擁有多少金錢及地位,而是個人之付出和愛的能力。耶穌在受難的那一刻自不自由?他的肉體被釘困,但靈魂卻不被禁錮!自由的寬度取決於愛的深度。
證嚴上人一生絕少個人的休閒活動,他也沒有出國旅閱古跡勝景、親歷名山古剎。他的作息時時刻刻都是在為人群社會付出,他不自由嗎?他常說在慈濟人身上,看到最美好的心靈風光。上人的一生不為自已累積財富,只求眾生能得安樂,他的生命不正是因此而獲致永恆之價值嗎!
社會上常常報導三十歲就累積上億資產的傳奇故事,但是許多慈濟志工年紀輕輕就開始為社會付出愛心,到現在已經白髮蒼蒼,仍心心念著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他們的故事會更不值得肯定嗎?
物質化個人,是資本主義對於個人生命價值最大的斲傷,到頭來人變成是集體資本製造機器的一個環節罷了。連個人的休閒方式都被資本化、市場化,亦是集體化。個人在資本市場的機制中反而不見了、消融了。一切都換算成資本市場的一個數字或一個對價的工具。
如何把個人從這種不是以愛為導向的機制中脫離出來?如何把個人從物化的價值模式中甦醒過來,是佛教及慈濟世界給予今日世界最重要的一項思惟。這正是證嚴上人希望「以愛為管理,以戒為制度」的精神意義。在職場,或任何場域,人與人都能以互愛為信念,深信「道德是要求自己,不是用來要求別人。」凡事以身作則,別人有錯,我們更要率先做好。這樣的思惟營造的場域,是個人得以獲得真正自由及尊嚴的路徑。
不管處在何種時代,個人不離社會,社會不離個人。而組織中如果有愛,個人才真正受到尊重,個人才得以真正自由。人在生命中如果能夠去付出愛、無所求的愛,生命才不至於在物化中扭曲,才真正尋得生命終極永恆的價值。
這是證嚴上人教導弟子擺脫資本市場制約的兩大法寶。
所以志工放下手邊工作,到災區、到醫院、到一切貧苦病苦之地,守護生命、守護愛,這是愛一切眾生。而不論人的生命、大自然的高山大海、一草一木、一花一葉,乃至一張紙、一個空罐子,都是有情眾生,都要我們去珍惜去愛護,這是上人給予慈濟志工的教導。
愛護生命、珍惜物命,十多萬位慈濟環保志工每天默默地在為大地付出,守護地球資源。他們做到珍惜物命的理想,不只要愛一切眾生,還要讓一切眾生都能愛人。這些人的生命價值都不是在資本累積及消費中尋得,不是在消耗地球資源中滿足自我,而是經由愛及利他的奉獻中獲得。
在世人汲汲營營於利益追逐、自我欲望滿足之際,世界貧富差距,人心衝突紛亂,而地球資源也加速面臨浩劫。人們是否繼續延續這樣追逐的道路,或是我們應該將已經歷時三個世紀的人類之追求,做透澈的覺醒和改變。
證嚴上人之思想及慈濟人實踐,或可提供現代人一個精神靈魂之出路,那就是愛和節制,或者以上人的話說,是「愛和戒」、克己而復禮。
慈濟思惟對科層化制度之反省
許多進了慈濟的人都感受到這裏的平等及多元的創發性。何謂多元創發性,亦即一件事情的提議和發想,絕不是某一個專屬單位負全責,而是許多不同的人。不論是慈濟志業體同仁、志工或其他社會人士,都可能發想提議做一件新的嘗試,而經由共同討論獲得共識後,著手進行並圓滿成功。這是多元創發的力量,與科層化組織、權責分明或壁壘分明有相當程度的不同。
從事人文工作的也可以做慈善工作,如大愛台於2006年提出送鉛筆到中國貴州的計畫,就十分成功;做醫療的醫生也可以投入慈善工作參加義診,或到貧戶家中打掃關懷等。醫生也參與人文工作,如擔任電視主持及積極寫書出版等。個人不被科層化局限及界定成為社會學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說的,個人在資本社會中,成為單面向的人。(Marcuse H.,1968/李亦華譯,1989)
慈濟四大志業一體,慈善、醫療、教育、人文之主管,每週固定在一起開志業策進會,彼此分享瞭解各個志業之脈動及發展,不只聆聽,還提出建言,或積極參與某些計畫。這是佛法無分別心之體現。佛弟子本應「總持一切法,行一切善…能斷勿疑,說法無畏,善能問答,說法無畏。」君子不器,更能包容每一個人的天分及創造力。
現代人無不被科層化之組織及專業主義之思想所約制,一生只做一件事,只瞭解某些特定的知識,只和特定的人交往,只對某些議題有興趣,對於其他廣泛的生命經驗一概關閉。在上人看來,這不是一個人的生命應有的發展;上人期許慈濟人都能真正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立體琉璃同心圓之圓形組織概說
有別於科層化的階級概念,慈濟組織中力行實踐人人平等的價值觀;慈濟世界人與人之間,沒有絕對的誰管理誰,而是人人以戒為制度,主動遵守規則,凡事溝通商量,取得共識,做事分工,並無明顯階級觀。不管來的是一位大企業家、老師、計程車司機,或是賣小吃的小生意人,來到慈濟做志工都是一視同仁。穿上慈濟制服,沒階級高低的分別,甫加入的大老闆或許要聽取一位做木工的資深志工之意見,以便有效地搭建好大愛屋。
今年七十歲的杜俊元先生是臺灣科技界傑出的知名企業家,他也同時擔任無給薪的大愛電視臺的董事長,可是他在高雄的社區裏跟所有的慈誠志工一樣,也發心幫忙鄰居掃街,而且必須值慈誠隊勤務指揮交通。
慈濟的志工組織力行上人於2005年提倡的四合一精神,分為合心、和氣、互愛、協力等四個圓圈組織。一個大都會設有一合心組,合心,是由資深並有德行之志工組成,負責精神傳承及社區重大工作之方向與定位。和氣組,是以區為單位,負責企劃協調工作之推動;互愛組則由幾個里的志工組成,負責工作之分配及執行;協力組是以里為單位,承擔社區工作之落實及完成。
四合一,無大小、無科層,因為最資深的合心,回到自己的鄰里和社區,一樣要聽協力組之指揮調度,出勤務、協助活動推展等。如慈濟榮董杜俊元,是高雄市的合心組,但是他一樣接受協力幹部的調度,幫忙掃地、協助指揮交通等等。這不同於當今金字塔型科層化的組織(清楚界定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關係)。
上人對組織的理念是希望把階級形態打破,建立一種上即下,下亦為上的立體琉璃同心圓之圓形組織。這種圓形組織的建立,仍需要人人謹守本分、彼此互愛、勤於溝通、善於協力,才能有效和諧達成任務。(潘煊,2004)
祥和社會之道-平等愛
佛陀曾說,五濁惡世有「劫濁、眾生濁、見濁、命濁、煩惱濁」。各種「濁」似乎在當今社會一一出現。人口激增所帶來的壓力,是「眾生濁」;許多牲畜一年數十億計的遭殺害,戰爭奪走多少人命,流行病讓家庭失去多少親人,這是命濁;科學專業越發達,人與人的意見越形分歧,乃至宗教間分裂越來越大,這是「見濁」;資本物質越發達,心靈越空虛,自殺憂鬱症逐漸成為社會頭號的殺手,這是「煩惱濁」。而這一切現象就是人類導致「劫濁」的宿命嗎?
證嚴上人說:「來不及!」正是因應「劫濁」的各種亂象,期待大家為災難世間多精進付出所產生的急迫感。他呼籲「心寬念純、美善人生」。人因為執著而苦惱、因貪婪而殺戮、因缺愛而煩惱,這一切都必須重回到如何保有一顆單純的心靈,及尋獲純淨的人與人之關係。
上人主張在一切情境下皆不對立,這是平等愛的一個關鍵意涵。身處劫濁之各種對立衝突,堅守用愛回應仇恨,是解決今日混亂世局的關鍵。
1998年,上人在印尼排華暴動之際,希望印尼慈濟人不要逃離,要用愛繼續回饋。2002年,雅加達發生水患,市區最髒亂的河流、又稱為黑色心臟的紅溪河災情慘重。居民原本沿河築屋,與垃圾為伍,慈濟印尼志工在上人的指示下,五管齊下—抽水、清垃圾、消毒、義診、蓋大愛屋。
一年後紅溪河亮麗起來,居民搬進大愛屋,幾世代的夢想竟這樣奇蹟式地實現,從此,印尼人開始對華人改觀。總統梅嘉瓦蒂親自到大愛村參觀,他留下深刻感動的記憶。印華對立氣氛逐漸消融,被禁止了三十多年學習華語的政策,竟然解凍了!華人也在印尼找到真正的尊嚴及地位。這種價值及尊嚴不是以金錢換取,而是用愛回應仇恨的甘美果實。
在宗教對立衝突的今日,印尼回教習經院在接受印尼慈濟志工幫助之後,他們開始學習靜思精舍自力更生的生活方式,開始研讀證嚴上人的《靜思語》。習經院每一間教室高掛證嚴上人的法照,回教學生兩千名開始穿上慈濟背心當志工。
而當慈濟在海嘯災區亞齊幫回教徒蓋清真寺時,一種化解人心對立的新文明已然產生。那即是宗教之真義,不僅是對於正確教義之堅持,而是能彼此同理和關愛。在這裏,覺悟的情感超越思想的執著,將不同的人們緊緊地連結在一起。
所以,「見濁」之化解來自情感、來自愛,而非思惟的論證。
慈濟宗門不是開宗立派,而是人類精神文明一個新的展現及體驗;是東西方文明經過幾百年衝突交融之後,一種全新的價值再造;在集體及個人、自利及利他、對立與共融之間,得出一個嶄新的見解及實踐方式。
經由利他,人才真正利己;經由群體,個人重獲寬闊的自由;經由尊重,人與人得以同理和諧;經由感恩,人將確認自我之價值,並達到社會平等公義。
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這些價值,個人都必須經由實踐而獲得,經由堅持不懈而得救。
註釋與參考文獻
註釋:
註1. 所謂「三苦」,即「苦苦」、「壞苦」、「行苦」。上人解
說,人們以「有漏五陰之身」,不斷帶著煩惱的業力來人間,五陰即色、受、想、行、識,又稱五蘊,時時與外境反應,稍不適意,就受煩惱逼迫,為了自身之苦而苦,稱為「苦苦」。
人間本來是苦,知苦諦才能體真理。有福之人一生鮮遇逆境,一路安然成長,生活順意,然而有朝一日「樂相壞時,苦相即至」,無常瞬至,福享盡了,苦相就會現前。上人說,世間有形之物,都會不斷地遷變,依循成、住、壞、空,老成凋謝,絕對無法永遠停駐留存,人的身體也有生、老、病、死的現相,故言「有漏之法,四相遷流,常不安穩」,這就是「行苦」;遷變至終,亦難逃「壞苦」。
參考文獻:
- 太虛大師(1987)。《法華經教釋》。高雄:佛光文化。
- 老子(2004)。《老子》。發達網。
- 李亦華譯(1989)。《單面向的人》。廣州:南方出版社。(原書Marcuse H.〔1968〕.One-Dimensional Man.US:Beacon Press.)
- 施康強譯(1999)。《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台北:貓頭鷹出版社。(原書Braudel F.〔1979〕.Civilisation materielle,economie et capitalisme. PARIS:Armand Colin)。
- 李中華(2006)。《新譯六祖壇經》。台北:三民。
- 聖經 。台北:聖經公會。
- 董樂山譯(2000)。《西方人文主義傳統》。台北:究竟出版社。(原書Bullock A.〔1985〕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 .Canada:NORTON.)
- 聖嚴法師(1999)。《金剛經》。台北:法鼓。
- 劉嵩(製作人、導演)(2005)。台灣人物誌:證嚴法師【影片】。(Discovery Channel: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319號12樓)。
- 潘煊(2004)。《證嚴法師: 琉璃同心圓》。台北:天下文化。
- 謝宗林、李華夏譯(2000)。《國富論》。台北:先覺出版社。(原書Smith A.〔1789〕.The Wealth of Nations. Franklin:Franklin Library.)
- 證嚴法師(2001)。《無量義經》。台北:慈濟文化。
- 證嚴上人(1995)。 <尊重生命價值,掘出愛心湧泉>,《慈濟月刊》,477。
- 釋證嚴(2000)。《 靜思語》。台北:靜思文化。
- 釋德凡(編撰)(2006)。《 證嚴上人納履足跡二○○六年冬之卷》。台北:靜思文化。
- 釋德凡(編撰)(2000)。《證嚴上人納履足跡二○○○年》。台北:靜思文化。
- Formm E.(2006). The Art of Loving.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 Maslow A.(1943).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Classic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50,370-396.
- Sachs J.(2005). The End of Poverty.England: Penguin Books Ltd.
本文轉載自慈濟大愛網 - 慈濟宗門的人文精神與思想略說